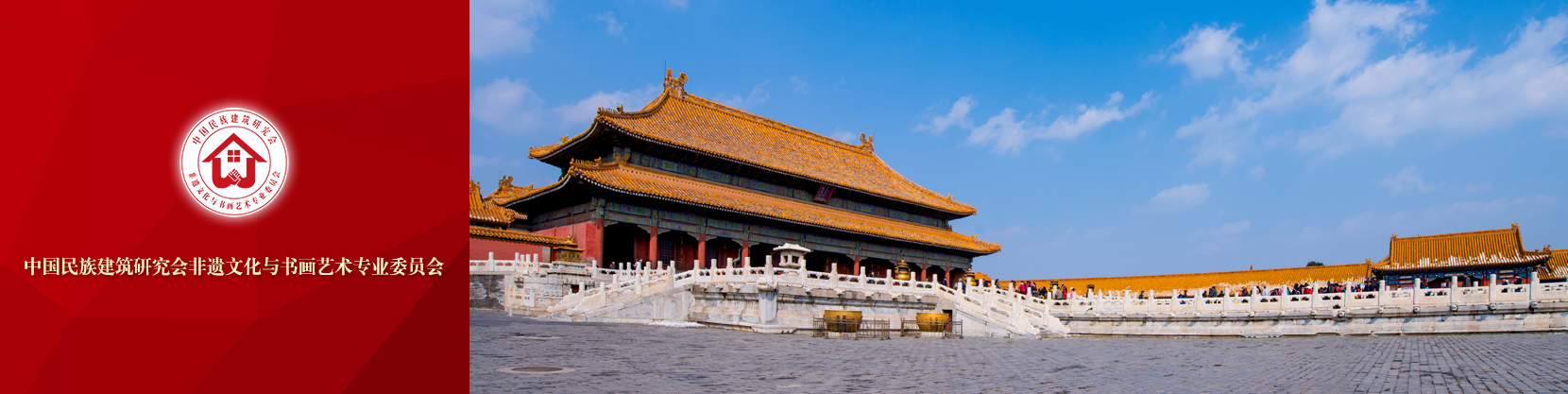人们常常会对曾经有过电话交往或者网络联系的人有种猜测,一旦面对面时还可能产生再认识的感觉:或意外,或与判断不差分毫。我与启功先生的两种场合的认识,既不能说分毫不差,也不能说出乎意料,只能说与众不同。
当然,我是先给他打过电话的。
那时我握着书界友人给的号码,在北京永安路106号光明日报社文艺部那个顶头三楼办公室里给启功先生打电话,心里有些忐忑。那是30年前,人们没有网络,没有搜索引擎,你了解一个人需四处找他的资料、他的书、他的行踪、他的作品。好在我有上过北师大并聆听过启功先生讲课的妹妹,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很多细节。妹妹说,那是一个极其幽默、极其可爱的老先生!他不照本宣科,也不循规蹈矩;他是历史大辞典,也是文学图书馆。他说文解字,他妙语连珠。上他的课,你学古代字体,你学诗文声律。你开心,你受益。他是最好的教育学家!
我就这样积攒了不少人们的传说,包括他是雍正皇帝后代等真实的故事。直到打电话那天我依然不敢确定这位老先生会不会答应给我们新的“艺术版”题个刊头字。
电话那边传来了听起来很温和的声音:“只写艺术两个字? ”
“是的。 ”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可惜,请这么一位受人敬仰的大书法家写字居然只要两个字。
“横写还是竖写? ”他问。声音不高不低,猜不出年龄,也猜不出他的表情,没有口音,而且很清晰。
“横竖各一个。 ”我真的不好意思,不知老先生对电话这边这个幼稚的女编辑会怎么想。而且我还挺啰嗦,又问了一句:“可以吗? ”
我脑子里想象他的样子,可能如照片上和传说中的:白发,戴眼镜,坐在满墙书画的房间桌子前挥毫。
“你说可以就可以,我得听你们的,你怎么问起我来了? ”
他说的没错啊!我很不好意思。随后我们讨论了繁体或简体以及落款等问题。末了,他问:“什么时候要? ”
“最好早一些。 ”
毕竟年轻,我的话几乎就是冲出去的。脱口后才想起给我号码的美术界人士叮嘱,人家说对高手大师级的人物可不能像编辑催稿件那样的急迫。想到这里,我赶紧解释,生怕对方觉得我不礼貌:“因为要做刊头的话我们美编可能还要加个花边什么的,修饰一下。 ”虽然事实也的确如此,可我依然觉得我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可笑:那么大的书法家的字本身就是艺术,哪里还需要外加什么去点缀呢!画蛇添足!
“嗬,用得着那么高级? ”老先生听起来倒一点也没有被冒犯的意思,相反却饶有兴趣。这让我放下心来。又说了点客套话,末了,我问他:
“请问您家进师大门以后怎么走呢? ”
“那你电话是打哪儿来的?“他又笑呵呵地反问。
我好像在那里呆住了,觉得很尴尬,可又很轻松。因为从他和我的对话里,我丝毫听不出一星点儿被仰视者们常有的傲慢和拿腔作调,相反那声音很普通、很平常。“是书法界的朋友提供的。 ”我如实告知。
老先生不再追问下去了,很耐心地很有条理地告诉我:你进北师大的门口以后,这么这么先往右,然后这么这么再往左……他说得很细心,很清楚。
按他说的,我后来真的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家。
那是很窄的楼梯,很一般人家的门口。
摁了几下门铃,静等。没有动静。我发现门铃坏了,于是便敲起门来。
在等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门玻璃上贴着的几个“告示” ,有先生作息时刻表;有前来讨字者须知等等。字迹看起来是秘书或者助手写的。可以想象老先生怎样不断地被打扰了。
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,我知道启功先生无儿无女,便猜测可能是外甥或侄子这样的亲戚。随着门的打开,就有声音从一进门左边的房间里传了出来,很是亲切。定睛一看,就看到了坐在写字台旁边的那个人——穿着很普通的厚衣裤,胖胖的,脸有些圆,眼睛也不大,如弥勒佛的样,不仅透着和气,还带有一些老年人的俏皮。此时他正笑吟吟的,盯着我这个前来讨字的年轻人。
我知道,这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启功!
他的样子,他的语气,他的和善,与我的想象很吻合。他使我立即不再有话筒边的那种窘迫了,而且他有一些真正大师们特有的对年轻人的宽容。我趁机环顾他所在的房间:书多,椅子多,而且上面都搭放着刚刚或早已写好的字,有的看上去墨迹未干,也有写好的宣纸,卷成一个个卷儿,放在一堆。这个场面似乎与我的想象比较接近。
关于这次拜访,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过《去启功先生家小坐》的散文。文中详细地记录了我所看到的启功,尤其是先生写字的精彩过程。我记得那次写字他写过三次,满意两个。找来了三两个印章,选了一个,很沉着熟练地盖上。我因怕印泥难干,便天真地用嘴去吹。老先生抬抬眼皮看看我,然后自顾自,变戏法儿似的在散发着馨香的红印处撒了几撮儿白白的粉;随后又拿来一支干毛笔,轻轻地一扫:印泥处不再油湿了,“启功”两个字清朗朗地显现出来。
这么近地看启功写字,实在是很过瘾。本想说点什么,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。原来北师大派人送信来了。听寒暄,是先生很熟悉的同事。他一边送人出门一边咒骂自己的腿:“瞧我这半身不遂,只能用一条腿走路,全是那缺德的写字给弄的! ”
在场的人都笑。“那为什么不吃药? ”我问。
“天生就讨厌吃药! ”
“您不妨试试,吃点儿,肯定有效。 ”我这才叫吃盐吃的太少了,居然给老先生提建议。
“我不试。人不能以身试法,我是不能以身试药! ”他可真是一个又倔又怪的老头儿!“有一个老中医,挺有名,特地给我开了方子,让我吃药。我说,我不吃中药,尤其不吃你开的。那老中医很奇怪,问:我跟你有什么世代怨仇呢? ”老先生一边拆着信一边念叨,听得我忍不住直捂嘴笑。
老先生有点咳嗽,但似乎不严重。“我夜里是又失眠又咳嗽。这病还是双轨制的呢! ”
这下众人又被逗乐了,他却不笑,转身找来一本刊有他作品的画册赠我。在扉页题字时,因画册纸太滑,不沾墨,他于是又变戏法儿般找来了肥皂,将有墨汁的笔尖在肥皂上一蘸,便字迹清楚了。瞧,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又学了一招儿。
接着他的话茬儿,有人劝先生每早最好锻炼身体,走走路或者打打太极拳什么的。这当口,我突然想起当时正流行的气功,特别是想起了书界有人很得意地对我说过的话,现在我就把这句话转述给了启功,我说:人家说,写字也是一种气功呢!
本以为会得到老先生的赞许,至少是同感之类的。岂料他看着我,冲冲地说了一句拍案叫绝的话来:
“是启功,不是气功! ”
我当年写他的那篇散文就以这句话做了结尾。
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非遗文化与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
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非遗文化与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